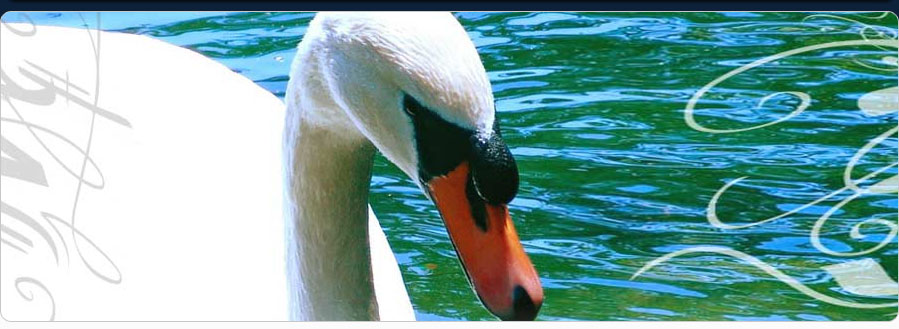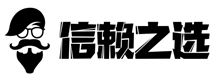佛教盂兰盆节乃缘起于《佛说盂兰盆经》。“盂兰盆”在梵语中称“Ullambana”,意思是 “救倒悬”,即用盆之类的器皿盛食供佛奉僧,以救倒悬之苦。饿鬼道中生活极苦,就像人被倒吊一样,必须借众僧的力量使他们脱离痛苦。而盂兰盆法会(盂兰盆会)是根据《佛说盂兰盆经》,以佛法供养三宝(佛法僧)功德,回向现生父母身体健康、延年益寿,超度历代考妣宗亲能速超圣地、莲品增上的佛教仪式。
盂兰盆会起源于 2700 年前印度佛陀时代。据《大盆净土经》载:印度频婆娑罗王、须达长者和茉莉夫人等皆曾依《佛说盂兰盆经》,造五百金盆供养佛及僧众,以灭除七世父母的罪业。又《佛说盂兰盆经》亦载: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目连,以天眼通观见其母亲投生饿鬼道,皮骨相连,日夜受苦,于是手持钵饭给母亲食用;然而目连的母亲因恶业受报的缘故,饭食还没入口,就全部变成火炭。目连为拯救母亲脱离苦趣,向佛陀请示解救的方法。目连依佛陀的慈示奉行,最终如愿以偿。正因此缘,佛陀乃再次慈悲叮咛善男善女:“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中常忆父母,供养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顺慈忆所生父母,乃至七世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
在中国,《佛说盂兰盆经》因西晋竺法护翻译,特别强调供养十方自恣僧,以报答双亲养育之恩,乃至度脱七世父母的思想,与中国崇尚孝道的传统相符,经历代帝王的提倡而盛行不衰。后世遂于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法会,斋僧供佛,沿袭成例。

传说中国最早行盂兰盆会是在梁武帝时代,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载:“大同四年(538年),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释氏六帖》也记载:“盆供五百,武帝送盆⋯⋯”宗懔《荆楚岁时记》则记载着当时盂兰盆法会盛况:“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自此以后,历代帝王臣民多遵佛制兴盂兰盆会,以报答父母、祖先恩德。南北朝时期佛教势力登峰造极,佛教思想漫延于朝野上下,无论是皇帝丞相,还是黎民百姓都深受佛教的影响,有的帝王动辄舍身寺院,甘当寺奴。由于佛教思想的盛行,各种习俗活动也取得众佛教信徒的认同。据《颜氏家训》卷二载:“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颜之推临终前告诫家人,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要奉盆祭祖,反映出当时北方也有盂兰盆信仰。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盂兰盆会已相当普遍,此时的盂兰盆法会是奉盆入寺供养,一切依佛门仪式举行。
赵翼《陔余丛考》载,北魏时已出现“三元”说:“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因道教崇奉天官、地官、水官三神祇,七月十五日是地官赦罪日,道教徒依据《佛说盂兰盆经》编撰《玄都大献经》,接受 “救拔饿鬼”的主旨,于是中元日“地官赦罪” 有了“赦免饿鬼”的含义。道经与佛经暗合,道门中元节与佛门盆节趋同,中古道教与佛教既互相斗争、又互相渗透,是以佛门盆节与道教中元节同日并行。唐代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云:“年年僧自恣日,四事供养三尊,宗密依之修崇,已历多载。兼讲其诰,用是未闻,今因归乡,依日开道俗耆艾,悲喜遵行。”[8]可见此时盂兰盆节已成僧尼道俗并行的节日。
自唐高祖、太宗以来,帝王大多信奉佛教,故盂兰盆法会于唐代宫廷十分盛行。《法苑珠林》载:“(唐高宗时)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举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不一。”此时信众献盆供者亦多。到了武则天称帝时(690―704 年),盂兰盆斋法会规模更是盛况空前,杨炯《盂兰盆赋》即说明了则天如意元年(692 年)法会盛大之景象。至玄宗开元年间(713―741 年),皇室中尚署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亦照例进盂兰盆贡献诸寺。代宗崇佛, “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德宗继位后虽取消内道场,罢内出盂兰盆,然唐代民间仍热衷佛事,德宗贞元年间崔炜在南海,中元日看到番禺人多在佛庙内陈设珍异物品,集百戏于开元寺。
纵使到了唐武宗时毁佛,然盂兰盆会依旧盛行。此时长安亦举行盛大之盂兰盆会。日本僧人圆仁即记述唐武宗会昌四年(844 年)长安诸寺盆节盛况:“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盂兰盆会在七月十五日举行)。诸寺作花蜡花钘,假花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盂兰盆节已然成了唐代民众广泛参与的盛节。

宋代以后,佛寺设盂兰盆法会,民间祀祖先、烧冥器衣物、焚钱山的风气转盛,盂兰盆法会从“供养”变为“荐亡”。天选团队盂兰盆上插有目连尊者或目连救母的造像,并于坛法完毕之后,用纸币焚化之。中元前后三日悬灯三夜,演出 “目连救母”的戏码,印送《目连经》(即《佛说盂兰盆经》)。与唐代相较,宋代已无仙宫胜景的陈设,道教色彩已褪去许多,特别是印卖《目连经》一事,显示老百姓对此经典的流通颇为主动,而“目连救母”的故事也从唐代说唱变文演变成杂剧,并成为中元时节的专属剧目。元、明时代的中元盂兰盆会则在宋代的基础上,增添烟火蜂炮、夜放莲花水灯(谓之“照冥”)。到了清代,中元盂兰盆会更是热闹,搭建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焰口、扎糊法船、放燃河灯。小儿夕执长柄荷叶灯,结伴参与斗灯会等,有些节俗与台湾现今所见者大同小异。
总之,盂兰盆节缘起于《佛说盂兰盆经》,而此经文是一部宣扬佛家孝道思想的经典,由于经文中的用字遣词及历算方式等内容皆与中国传统民俗息息相关,因此有许多佛教学者将之视为中国人自撰的伪经,而假托为西晋竺法护所译。《佛说盂兰盆经》因与孝道文化有直接关系,自然对中国佛教及民俗中元节庆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而盂兰盆会之所以深得民心,实因法会强调藉供养十方自恣僧,以达慈孝双亲,乃至度脱七世父母的思想,与中国儒家崇尚孝道、慎终追远的伦理传统不谋而合。加上帝王的倡导,盂兰盆会很快地由寺院走向民间,由佛教节日成为民间节日。武则天如意元年洛阳南门举行的盂兰盆会空前盛况,不仅法会上有大量的佛教徒参加,而且统治者、士大夫都参与其中。同时为了显示盛唐国威,统治者还 “纵吐蕃使者以观之”。为此,杨炯乃以赋体形式写下了有名的《盂兰盆赋》。

两汉之际,由印度、西域传来的佛教,逐步展开其中国化的历程。佛教鼓励出家,本与孝道相悖,但中国化佛教不仅重孝道,魏晋南北朝更因轮回观念,而演化为超度父母死后之佛事,《父母恩重经》与《盂兰盆经》即大力阐发孝道,佛教乃更广泛地传播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呈衰微现象,但儒家“孝悌”之伦理观念始终是统治阶级的一贯宗旨。梁武帝萧衍曾提出“三教同源”说,认为三教可以相互辉映,并称儒释道三教始祖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为“三圣”。他广建佛寺,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不仅大力推动佛教的广播流传,而且直接促成了佛教盂兰盆会的民间化节日形成。
由于南朝时期之君王及文人学士多崇信佛教,此时崇拜佛教的活动,如造像、建寺、立塔、讲经、受戒、法会等,都成了文学描写的题材,是以崇佛文学大盛。以赋作为例,梁武帝《净业赋》《孝思赋》,萧子云《玄圃园讲赋》、萧子晖《讲赋》和江总《修心赋》等,或宣说佛理,或希冀皈依佛门潜心修身,不仅辞藻华丽,且对偶精巧、音律谐畅,已具颇强之艺术感染力。隋唐时期,佛教更普遍存在于社会精神文化领域里。然而唐代因道教始祖老子姓李,故唐朝帝王自称为“老子后裔”,并尊奉道教为“皇族宗教”,由于皇族始终扶植和崇奉道教,故促使道教在教理、教义和斋醮仪式方面有较大的发展。
此时士大夫的诗文中,往往笼罩着一种庄严肃穆、和谐凝重的神秘宗教气氛,透露出恢宏的气象。如卢照邻《五悲文》中之《悲人生》,比较了儒道佛三家,说明佛教是何等的辉煌灿烂,何等的凌厉奋发,何等的磊落坦荡,何等的睿智明敏!可见有部分士大夫仍然认为佛教高妙,远远超过儒道二家。
事实上,唐代帝王自高祖武德七年(624 年)起就建立了“三教论议”制度,此后几乎历代相承。三教论议的实质,是以儒家为核心。尤其在孝道上,佛道两家都积极迎合儒家思想,并且在相互争锋中都逐渐确立了各自的孝道思想,其中佛教孝亲的中土化,更促进了下层民众对佛教的崇奉信仰。武则天于三教中对佛教特别推崇,因其童年时期曾受母亲影响出入佛寺,且其于唐太宗死后被送入感业寺为尼,虽然《僧道并重敕》一文说其对佛、道崇奉之心相同,但武则天似有以“佛授”代“天授”、借“佛威”以壮“帝威”、借佛以合法巩固其女皇地位的意图。尤其武则天以周代唐后,为削弱唐宗室的政治影响而贬低老子,扶持佛教,因此对于三教“武则天最重视佛教”。是以初唐时期,文士有以虔敬笔墨赞叹释迦牟尼佛者,如王勃《释迦佛赋》;有铺陈佛教盂兰法会之仪式者,如杨炯《盂兰盆赋》;有专写佛教寺庙者,如沈佺期《峡山寺赋并序》;而杨炯的《盂兰盆赋》不仅受道教设坛摆供祭祀法会的影响,更是融佛教“孝道”与儒家“孝悌”文化为一体,将洛阳盂兰盆法会仪式铺陈详尽的佳作。

有唐一代,除武宗朝等少数的时间段内政府对佛教采取打压的政策,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因为佛教能为其统治服务,朝廷对于佛教是相当推崇的,作为佛教节日的盂兰盆节也得到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其雅丽。”在《书》也有记载:“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喜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而识者嗤其不典,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由此可以得知武则天和代宗统治时对于盂兰盆节是大力提倡的,甚至在唐代宗之时将举行盂兰盆会作为国家祭祖活动中的定制。
除此之外,在《唐六典》中也有记载:“中尚署令掌供郊祀之圭璧……每年二月二日,进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寒食,进毯,兼杂彩鸡子;五月五日,进百索绶带;夏至,进雷车;七月七日,进七孔金细针;十五日,进盂兰盆;腊日,进口脂、衣香囊。”如果说武则天和代宗时期是因为推崇佛教才提倡盂兰盆节的话,那么《唐六典》中记载由中尚署令管理盂兰盆节一事则说明在唐代宫廷之内庆祝盂兰盆节已经成为常制,并不因为当政者崇佛或是抑佛而有所改变,也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在长安举行的盂兰盆节的活动往往是由政府组织,其费用也是由官方支给的。

唐代的盂兰盆节相较前代来说有了很大变化,盂兰盆节开始由佛寺走向民间,其活动不再是简单的盂兰盆斋了,而是融入了许多中国旧有的民俗内容,变得更贴近百姓的生活,逐渐由佛教性的节日转变为民俗性的节日。
唐代盂兰盆节的活动较前代增加不少,自中唐以来,每逢盂兰盆节日常有群众性的集会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项:(1)拜祭祖先的亡灵。(2)设食燃烛荐享无主冤魂。(3)“斋田头”、“祀田神”。(4)举行盂兰盆斋。(5)放江灯。(6)演出“目连救母”变文。除以上的所列之外,据李斌城先生所考,中唐以后,在不同的地区盂兰盆节的活动也有所不同。在岭南,百姓这一天陈设珍异,集演百戏;在建康,有人于是日出游瓦官寺,所在“士女阗咽,男女混杂”。僧俗大众在节日集会于寺庙,既是祀会,又是共同欣赏娱乐活动。

唐代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进一步加深, 而作为佛教节日的盂兰盆节逐渐民俗化的过程恰好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侧面反映。在唐代韩鄂所著的风俗志《岁华纪丽》中记载:“孟秋之望,中气之辰。道门宝盖,献在中元;释门兰盆,盛于此日。”诗人崔元翰在为唐德宗在盂兰盆节所写的应制诗中,也把盂兰盆节称为“中元”。据《太平广记》卷 34 记载:“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由此可见,在唐代盂兰盆节有渐与中元节合流的趋势,并且盂兰盆节的习俗已普及于民间。
盂兰盆节与中元节并行是中国古代宗教节日的一大奇观,自南朝至宋代,两节并行达六百年之久。在宋代孟老元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中元前一日,即卖练叶,享祀时铺衬卓面,又卖麻谷窠儿,亦是系在卓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这些习俗说明到北宋之时,佛教的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已经互相交杂融合,两节统称为中元,这时的盂兰盆节已由佛教的斋节变为同清明、端午一样为广大普通民众所喜的民俗性节日了。

盂兰盆节应是在隋唐之时传入日本的,根据日本学者宫家准考证:日本第一次举行盂兰盆会是在佛教传入后的推古天皇十四年(606),记载盂兰盆会由来的《盂兰盆经》也被记录在《日本书纪》的齐明纪五年(659)7 月条目中。在当时唐王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佛教都在此时传入了日本,对日本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作为佛教节日的盂兰盆节理应是在此时同佛教一起传入日本的。盂兰盆节在传入日本之初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其主要内容仍是祭祖、举行盂兰盆会、祈愿农作物丰收等,这种情况从盂兰盆节传入日本开始延续到平安时代末期,之后中国式的节日习俗渐渐出现了日本化的倾向。
如同盂兰盆节在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一样,其在日本也受到了神道教思想的影响,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祭祀日本本土的天神地祇,同时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在日本社会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而,盂兰盆节在日本的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而在主旨和内容方面有所改变。以日本古城京都所举行的盂兰盆会为例,其主要内容为六道参拜、五山送祖灵火、六地藏拜庙和在念佛寺举行千灯供养等,这与中国传统的盂兰盆节习俗有较大差异。
从上述保留下来的盂兰盆节的活动来看,日本的盂兰盆节既有佛教斋节原来的习俗,也有受到日本神道教崇拜亡灵、崇拜自然之神传统所产生的习俗,盂兰盆节在日本的传播过程恰好说明外来文化要融入一个地区,必须要吸收这一地区旧有的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传播发展。

关于朝鲜的盂兰盆节,最早的记载是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儒礼尼师今》中:“九年……王既定六部,中分为二,使王女二人,各率部内女子,分朋造党,自秋七月既望每日早集大部之庭绩麻,乙夜而罢。”由此可知,在新罗王朝活跃的时代,盂兰盆节已经在朝鲜半岛流传开来。
朝鲜的盂兰盆节又称“百中”节,“百中”一词的解释有多种,但其最开始的本意应该与道教“中元” 之意相同。其后也加入了许多其他的含义,如洪锡谟《东国岁时记·中元》:“又按盂兰盆经,目莲比兵具五味百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今所云百种日似指百果也。”这里的“百中”指的是“百果”。而在李植的《泽堂答倭人问目》中记载:“七月十五日,谓之中元……王女率六部女子。自七月既望,早集大部庭绩麻,至八月十五日考功多少,负者置酒食以谢胜者,相与歌舞作百戏而罢。”李植认为“百中”指的应是 “百戏”。在朝鲜史籍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明盂兰盆节在朝鲜得到传播后已经是一个民俗化的节日,其祭祀农神,祈祷丰收以及游戏娱乐的含义已经胜过祭祖奉斋的传统寓意,这是盂兰盆节在异域进一步民俗化的表现。